田子坊:空间品牌的社会命名
- 汽车
- 2025-02-25 12:24:09
- 8
上海泰康路上的田子坊在今日上海遐迩闻名,二十多年前它还只是一处普通的上海弄堂,更确切地说,那时的泰康路还没有田子坊。一场兼顾民生利益、社会公正、创新产业和城市文脉的包容性旧区改造实验,将田子坊做成了上海知名度最高的创意产业品牌,成为上海的一处城市地标和文化名片。自创设以来,田子坊已荣获上海市和国家授予的多项荣誉称号,斩获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上海十大时尚地标、最具影响力品牌等殊荣。将旧式里弄改造成人气社区,田子坊走的路线与上海新天地完全不同,其成功有诸多原因,从品牌建构的意义上看,“社会命名”是田子坊产业空间获得巨大影响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其中的深意是,成功不仅是做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就本案而言,此系三重社会命名:陈逸飞和黄永玉完成的艺术空间的命名,厉无畏完成的产业空间命名,以及阮仪三完成的历史空间命名。本篇分析借鉴的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命名理论,聚焦于社会命名作为一种现实建构论的方法论,在传播学之外提供了一种品牌建构的社会学解释。

布尔迪厄社会命名论:名号、名堂、名位
在布尔迪厄眼里,社会首先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世界,所谓“有名有姓”,意味着社会不只是一种客观实在,也是一种被表象、被命名的实在。如此,“社会科学处理的就是已命名的、已分类的现实,它们带有各种专门名词和普通名词以及称号、符号和缩略词”。但并非任何人说的语词都有建构实在的作用,只有那些被授权的人在严肃场合表达的正式话语才具有制度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权威在语言之外。要处理的是这些语词是由谁在怎样的场合及怎样给出的。有效的社会命名不单是语言的效力,更是制度的效力,这样,“社会科学必须将有关命名(naming)的社会操作以及使命名得以完成的制度仪式作为其研究对象”。了解命名的社会操作,了解使命名完成的制度仪式,就是了解命名的权威是怎样产生的。社会命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命名或社会表象,“不只是反映社会关系,还有助于构建这些关系,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人们就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这就进入布尔迪厄要求的更高层次的分析:“必须研究词语在社会现实的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建构现实的命名行为数不胜数,“例如婚姻或者割礼,头衔或学位的授予,骑士称号的赋予,官员的任命,通告或表彰,某种品质标签的赋予,或者通过署名或首字母予以确认”,一旦确认,“意味着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向某人或某事物赋予这种或那种职位或者特权”,这岂非一种“圣职授予”,或“点石成金”?是的,布尔迪厄直呼上述命名行为为“社会巫术行为”。但巫术既不靠“欺世盗名”,也不靠“冒名顶替”,变俗物为圣物,一是由“被广泛认同的权威所执行”,二是“在于群体的确信”。概言之,布尔迪厄的社会命名论,不只是分类社会世界之名号论(名词性的),也是描述社会世界之名堂论(形容词性的),更是建构社会世界之名位论(动词性的)。
田子坊空间的三重社会命名
1.从泰康路到田子坊:从俗物到“圣物”
田子坊产业空间品牌的第一重建构或第一重社会命名是从两位艺术大师陈逸飞和黄永玉开始的。
陈逸飞来到之前,没有田子坊只有泰康路,最初的计划是从当地主官梦想把泰康路改造成文化一条街开始的。上级对街道政府尝试利用闲置厂房来做文化无意反对,还乐观其成。开发者有梦想但缺理念,虽殚精竭虑,尝试的文化街区最终并没有火起来。陈逸飞的加入,才让泰康路变成了田子坊,或让一条籍籍无名的寻常马路变成一个遐迩闻名的新文化产业空间。它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在以陈逸飞为代表的具有世界主义眼光和纽约SOHO理念的艺术家们发现泰康路旧里空间的美学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陈逸飞工作室落户泰康路210弄后,各路艺术家闻风而动,相继入驻。从旧厂房中发现价值,只有熟悉SOHO理念的艺术家才有如此眼光;而“化腐朽为神奇”,将本地人不屑一顾的闲置厂房改造成人见人爱的艺术空间,更是只有熟悉当今世界各种最新设计流派风格且有高深造诣的艺术家才具备此能力。旧厂房在本地人眼里就是废弃的无用空间,也正因为本地人没有SOHO眼光,泰康路有待出租的厂房一直无人问津。田子坊的先驱者多为有过旅居海外经验的大艺术家不是偶然的。因为大拆大建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盛行时,保护性改造的SOHO理念在西方已经成熟。海外经验加上专业眼光,很容易让陈逸飞等中国顶尖艺术家们发现在一片拆除声中为国人所忽视的旧里有机更新的可能性。他们在本地人看不出所以然也看不起的地方看出了大大的所以然,也从最本地化的空间里创造出最具世界主义的社区来。
如果说陈逸飞们对泰康路空间的SOHO改造或SOHO命名是功能性(将工厂空间艺术化、美学化)的话,那么,黄永玉以国史可考的第一位画家田子方之名将泰康路改名为“田子坊”,此命名则是十足社会性的和符号性的。从泰康路到田子坊,这是意义非同寻常的社会命名:分类和神化。“田子坊”的命名就将一个“俗物”变成了“圣物”,进而与其他基于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项目,包括与田子坊一街之隔的日月光中心广场完全区别开来。去田子坊,人们是去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打卡;而对多数人来说,日月光中心广场只是一个消费主义的热门场所。
按布尔迪厄的分类理论,黄永玉所做的不只是对一处空间的改名,更是一种符号资本的生产。黄永玉的命名并非官方行为,并不具有国家命名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但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并非只有国家命名或官方分类一个来源,诸如质量管理标准ISO9000与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的认证都是非政府的第三方认证,与国际标准一样都具有普遍象征效力。由具有业界卓越地位和广泛社会声望的艺术大师参与空间改造和空间命名,实在也具有“社会点金术”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艺术地位和文化声望代表了布尔迪厄所说的被广泛认可的文化权威。然而,田子坊的命名最初是不被主张拆除田子坊街区的计划方承认的,认可“田子坊”之名,就等于认可这一命名建构现实的效力。在田子坊的去留方案处于争执阶段时,主张拆除田子坊的领导在现场断言这里只有泰康路,没有田子坊。田子坊实验团队反驳道:“若说田子坊是假的,新天地也是假的,从来只有太平桥,没有新天地。”“新天地”是开发商命名的,它之所以不被当地领导质疑,因为它本身就是政商合作的范本,是资本权力和公共权力的结合赋予“新天地”命名的合法性,“新天地”更被标榜为基于历史文脉保护的旧城改造的新模式。所以,透过名词的真假之争,我们应该看到实质上的文化权力之争、经济权力之争及开发模式之争。田子坊命名带来的真假之争,只是名义之争吗?当然不是,“但一定要表现为命名之争,因为社会世界就是被命名的世界,人们正是通过命名,创造命名去创造他们认为新的社会世界和社会空间”。
2.产业空间的命名:文化创意产业
陈逸飞的文化产业不仅引来更多的艺术企业家,也为田子坊赢得了中国创意产业发源地的荣誉,但此创意产业的命名必须有待社会科学家的发明,经济学名家厉无畏以创意产业园区之名定义田子坊,给了田子坊一个迥异于其他旧城更新项目之不可替代的身份。
创意产业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城市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级的兴起》,创意阶级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成员的工作是以“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为能事。这个阶级的高层创造核心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娱乐业创作家、演员、设计家、建筑师,以及现代社会的思想领袖,如非虚构作家、编辑、文化人物、智库研究者、分析家和其他思想创造者等。这个创造力的高层核心成员创造出易于转化和有广泛用途的新形式与新设计,如设计出一个可以大量制造、销售与使用的新产品,或提出一个可运用于许多方面的原理和策略,或创作出可一再演奏的曲子等。什么样的城市可以吸引创意阶级?第一,那些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生活方式和舒适物(amenity)的城市,它们可以吸引追求某种生活方式的创造性人士如音乐家、画家、技术人才等前来生活,然后发展职业。第二,城市的多样性本身吸引人。一个拥有不同的族群、年龄和另类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的社区就是一个信号:这是一个对外人开放的地方。第三,原真性是生活品质优越和城市令人愉悦的一个重要元素。原真性来源于社区的诸多方面,如历史建筑、有年头的街坊、音乐氛围或文化特质等。与现代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是,不是越现代的越技术主义的城市越能吸引具有原创能量的艺术家或艺术企业家,恰恰是保留着丰富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和街区,才是最适合创意产业诞生的地方,如此来看泰康路为何能得到陈逸飞等艺术家的青睐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田子坊实验之所以不乏世界最前沿的流行理念和话语,是因为这场改造一上来就是以纽约的SOHO为榜样的,声称要“将田子坊打造为上海的SOHO”,进而当田子坊遭遇被大拆大建项目取代面临生存危机时,实验者们寻求的也是从诸如“创意产业”即在西方刚刚流行的理念中获得合法性。2004年,为保住田子坊,开发团队请来经济学家厉无畏,厉无畏在《人民日报》上发文,以“创意产业”概念定义田子坊里由艺术工坊、设计工作室和美术画廊等集聚的产业。他首先回答了人们的疑问,何以许多文化创意产业会集聚于旧工厂、旧仓库?“不仅因为早期租金较便宜,又地处市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厂房、旧仓库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其敞露的屋梁架构又引人遐想,不知不觉促成一种思维的架构;加之老厂房、旧仓库开阔宽敞,可随意分割、重新布局,因此颇受艺术家青睐。”厉无畏继而界定文化创意产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辐射力。它渗透到各行各业,可大幅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如产品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潢、包装、商标、广告等,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他大胆断言,“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是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的两个抓手,培育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田子坊的实验,代表了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旧区改造的有机结合,“可以避免城市文脉的中断,不仅能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而且通过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洋、经典与流行的交叉融合,为城市增添了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景观,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使城市更具魅力,给人以城市的繁华感、文化底蕴的厚重感和时代的生机感”。
田子坊数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之所以又数次化险为夷,除了实验团队的坚持,学术精英的声援功不可没。厉无畏、阮仪三等学界领袖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央与地方党报上为田子坊的产业创新和空间创新所做的正名辩护,让田子坊实验尽得话语上的优势。而当田子坊路线获得学术精英的喝彩和声援时,体制内的两种权力,即地方政府代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精英代表的文化权力,既有冲突也有互补。厉无畏的工作不仅为田子坊的实验正名,也用一个全新的产业概念影响了上海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构想,并将“创业产业”的概念写进了2005年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天,厉无畏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而此声名就是从田子坊开始的,确切说是从界定田子坊创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命名工作开始的。
3.历史遗产空间的发现和命名:田子坊话语
以旧里保护的方式复兴内城空间,需要旧里留存的理由,具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为泰康路旧里历史建筑的丰富性提供了专业的论证,进而支持了田子坊空间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观点。
与田子坊相对,新天地也是标榜保护性改造而大获成功的旧里更新项目,新天地的石库门博物馆这样描述新天地:“老人们安顿了怀旧之情,年轻人发现了时尚和潮流。老外看她是地道中国的,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洋文化。”也许田子坊更配得上这个评价。阮仪三强调旧城更新要的是延年益寿而非返老还童。没有寻常“人家”,是阮仪三给新天地差评的主要理由。“小桥、流水、人家,没有‘人家’,再好的景致也诗意顿失。”笔者的评论是:“新天地之所以没有老上海的感性,根本在于它没有市民,没有真实的居民生活,从而没有石库门街区最常有的市井情调。它的老上海场地是消费主义且是绅士化的,所以仍然是与真正的本土脉络不相干的,这是一种伪上海(nostalgia)。”同济大学常青教授则批评被新天地保留的只是空间格局和外墙体,从屋架、地面到内部空间,都经过了改头换面的二次设计。在上海参加国际课程的外国学生,多半喜欢田子坊更胜过新天地,其主要的理由是新天地过分的商业主义。
新天地以老上海为卖点,老上海人明知道新天地并非他们曾经生活的老上海,但把他们曾急于逃离的旧里改造成上海开埠以来最好看的石库门景观,触动了他们集体记忆的柔软处,所以新天地的这一老上海的命名传奇被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了。但新天地的“老上海”是清场后的作品,它只有石库门的皮相,而没有石库门的物质内里和生活内里,尤其是石库门里弄生活的主角被完全清场了。新天地之所以被方家批评为假古董,至少就它做成后大打老上海的旗号而言是不算冤枉的。
肯定田子坊,并非它是真古董。在阮仪三看来,旧里保护的价值,首先在于这里有着最为丰富的上海民居类型,从充满乡土味的本地民居,到盛行上海的旧式石库门里弄,再到设备更摩登的新式里弄,甚至西式洋房。总之,即使从民居博物学的意义上来说,保留和有机更新泰康路里弄都价值重大。阮仪三是国家级的古城保护和修复专家,他为泰康路历史街坊的价值背书,与黄永玉、厉无畏对田子坊的社会命名的工作一脉相承,并更有巩固和深化。
为艺术家陈逸飞和建筑专家阮仪三都看好的田子坊,的确也因为其所在旧里的建筑空间的多样性提供了创意和想象的灵感,所以吸引了各路的创业者。不少业主就是冲着田子坊里弄的历史空间来的,赞赏这里有情调、有氛围、有味道、有生活。
当然,原生态上海里弄的田子坊并非原生态自然演化而成,正如本章前文所述,它是经历了激烈的话语竞争的一个社会命名的产物。田子坊纪事,其创新不仅在于创造了让老上海人大呼“灵格,灵格”的有原真性的老上海空间,还在于构建出一种“田子坊话语”。略去先前的艰难探索所用过的诸如“泰康路艺术街”之类的话语不论,真正形成局面的社会命名是从陈逸飞入驻泰康路210弄的旧工厂开始的,随后的古建筑保护及城市规划专家和经济学家的结盟让田子坊话语获得学理形态,最后厉无畏、阮仪三将他们学术的田子坊叙事通过强势媒体演绎和传播为公众话语。阮仪三以他一贯的激情为田子坊保留形态转换功能的更新方案背书,更对艺术家们的空间再利用再创造大加赞誉,说他们的创意让田子坊“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又突显了鲜活的时代特点,展现了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阮仪三喊出“保护上海‘苏荷’(SOHO)”的口号,如同他挺身保护水乡周庄时的姿态,要担当的岂止是一个名称,更是一项历史文脉传承的使命。
艺术精英创造了一个田子坊的空间传奇,并以田子坊之名将一件俗事变成了一个圣物;学术精英的话语则为田子坊建构了一个意义丰富的、正当性叙事:历史街区保护的正当性、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如此而成就了田子坊实验之于城市有机更新的名号、名堂和名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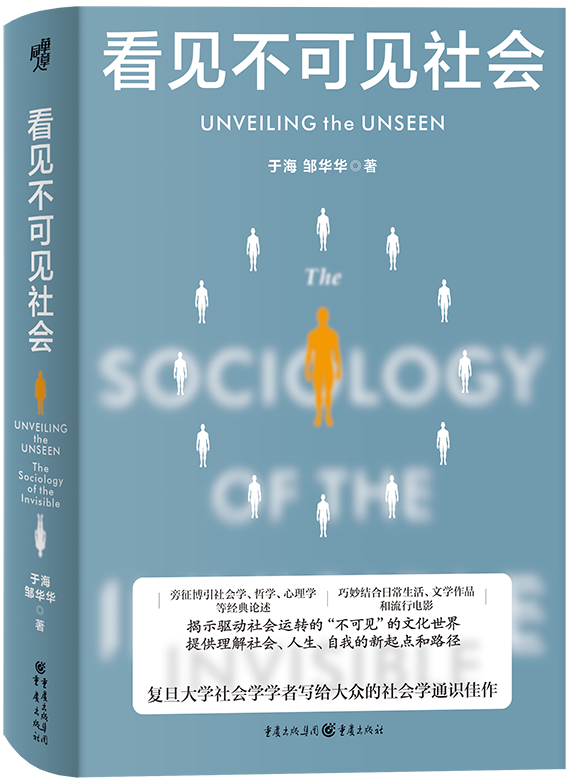
(本文摘自于海、邹华华著《看见不可见社会》,华章同人|重庆出版社,2025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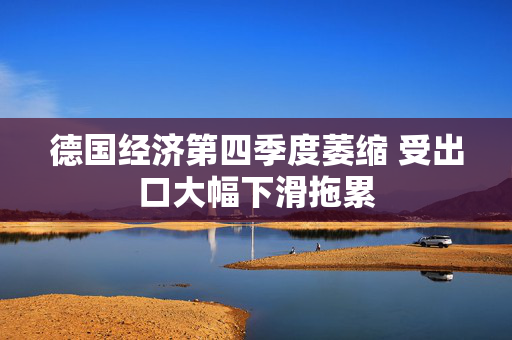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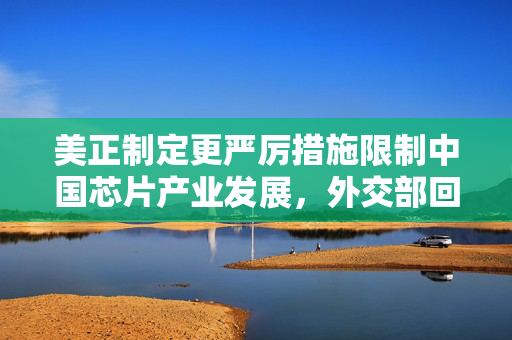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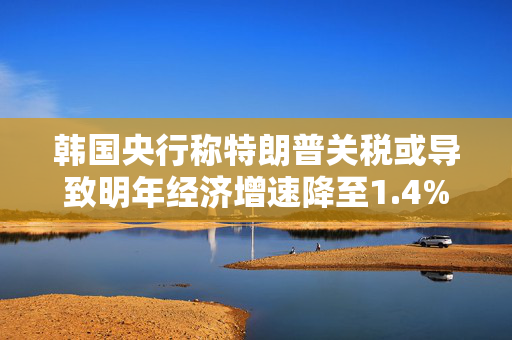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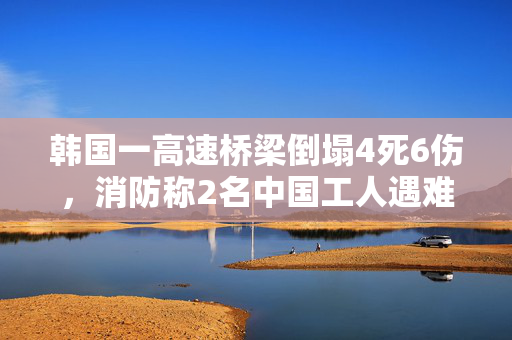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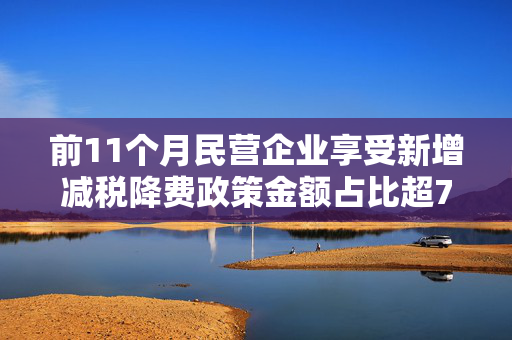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