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午餐会|孙扬:从救亡图存到改革开放——中国的艰难求索之路
- 文学
- 2025-02-19 15:04:12
- 17
学术午餐会是学术界常见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方式,无论是普林斯顿高研院、哈佛—燕京学社,还是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经常采用这种开放自由的形式开展讨论和对话活动。在温饱之后转而追寻美食和精神愉悦,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天性,作为他人的精心呈献之物,美食如此,知识亦然,两者皆不可辜负。
南京大学“学术午餐会”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开始于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2005年发起的学术冷餐会,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一百多场。今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打造的“南大读书人”文化空间正式启动。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新生学院联合开展的“学术午餐会”延续了南大读书文化的基因,邀请历史、哲学、文学、社科等领域的学者,带领来自新生学院的本科生们共读学术著作,让同学们接触到一流的学术资源,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学术素养。
本期活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孙扬副教授为同学们导读《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和《邓小平时代》两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启发同学们用历史的逻辑思考问题。以下是孙扬导读发言的文字稿整理。
历史知识的生成是“聚沙成塔”,强调时间、空间以及特殊性
在之前的读书会中,导读老师更多站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讨论问题。今天这两本书应该是本学期读书会中最不具理论性的书籍。这两本书也不是公认的经典,因为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难有像古代史那样举世公认的经典。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两本书?因为虽然关于历史,却是很近的历史,是大家仍然可以体验到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在某些程度上比较经验主义也比较朴素。所谓经验主义是指史学似乎比较排斥先验性的东西,理论带有先验性,而历史往往难以归纳,即将所有现象归纳起来总结出规律,在逻辑上也很难演绎。它更强调时间、空间以及特殊性。所谓朴素是指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前一个时代积累的材料,人们往往依据常识去解读。因此,历史知识的生成往往是“聚沙成塔”的过程。历史思维与其他学科的思维有所不同。我们经常提到“三大逻辑”,分别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历史逻辑是时间和空间的关联,任何人物和事件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间,受到前面的影响,也会在未来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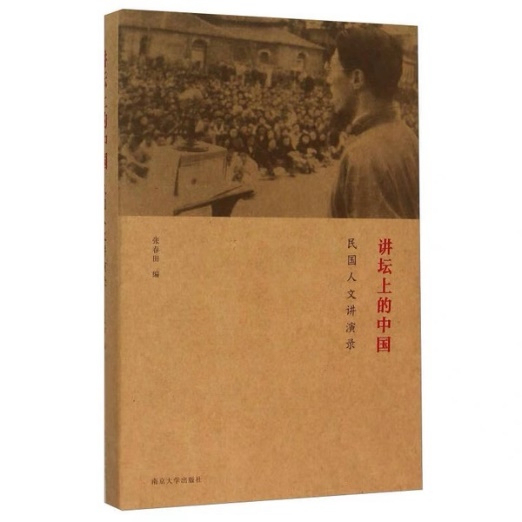
《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 张春田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它并非著作,是编者将民国时期著名人士的演讲汇编成书,在今天看来属于“史料”。同学们刚开始读这本书时,可能会有疑问,民国时期的演讲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什么价值?但读后就会发现许多问题是贯通的。这种贯通性,如果用一个具体形象去表达,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只要纪念碑在,我们就同处在一个历史纪元。纪念碑碑文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正文一共三句话、114个字。每句话都由时间起始。第一句话开头是“三年以来”,第二句话开头是“三十年以来”,第三句话开头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表达了近代中国革命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性。也正是因为碑文最后一句话中的“一千八百四十年”,揭示了我们同处历史纪元的时间起点。可以说,这个纪元的启动归于一个命题之中,那么,这个命题是什么?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延续数千年至今的文明。但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的碰撞中一触即溃?“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时间。战争从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开始,到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江面结束。为何那时结束?因为英军兵临当时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城市、朝廷在东部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截断长江和运河,漕粮无法北上,严重危及朝廷财政。英军到达南京之前清军抵抗是否激烈?在第二次定海之战中,三位总兵同日殉国。还有在镇江,江宁副都统海龄率部死守,八旗兵作战尤其勇猛,一些旗兵上阵前杀死妻儿,以防落入敌手受辱。然而,根据英国的《官方中国战争史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载,镇江之战,英军仅死亡37人,失踪3人,受伤128人。英军在镇江之战中的死亡人数,还是在两年战争中所有战役中最多的。虽然有历史学家质疑英方故意缩小伤亡人数,做了重新估计,但一般而言,战争伤亡以伤亡方统计为准。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激烈碰撞,就是以这样惨烈的结果收场的。
在阅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可能大家会有疑问,那时不少中国有识之士,为何对西方如此倾慕,认为只要照搬西方那一套,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渴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回想一下人类的历史进程,科学和技术、政治和文化在200多年前,有一次剧烈的变革。18世纪开始,两件事情出现在欧洲。一件是科学和技术层面的,也就是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另一件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民国人文讲演录》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到工业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也常常讲到法国大革命。“双元革命”推动了人类历史整体改变,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疑问具有伟大进步意义,试想,如果没有抗生素的发明,人类的寿命不会有今天这么长。虽然现代化是好事,但它却伴随着一件坏事向全世界扩散,这就是殖民主义。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把欧洲的准则赋予人类的普遍性,重新定义了“文明”与“野蛮”、“落后”与“先进”。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反抗列强侵略,又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是在何等激动的情绪下起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周恩来写了40多遍才挑选出最满意的一幅。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傍晚6点举行奠基仪式,毛主席铲了第一锹土,当纪念碑建成时,已是1958年4月。这座纪念碑凝聚着中国人民100多年前赴后继的牺牲和探索。纪念碑的北面碑心石料采自青岛浮山,是一整块最初重达300多吨的花岗岩,经开采、打磨减重再运到北京,耗费巨大人力。汉白玉主要采自北京房山,浮雕由八块主浮雕和两块装饰浮雕组成,反映从虎门销烟到渡江战役的八个历史事件。浮雕中的170个人物,都有真人模特。雕塑家们还特意请来解放军战士,要求他们做裸体模特,以便准确把握骨架和肌肉。许多战士害羞,要求保留一条短裤。此外,还要训练工匠学习西洋美术,从基础理论开始。就这样,人民英雄纪念碑耗时近9年才建起来。
近代中国的开场是如此悲怆,无数仁人志士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一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思考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向压迫自己的敌人学习。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从晚清到民国,无数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中国何时才算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1949年具有“创世纪”的重要性,而此后30年,中国筚路蓝缕,不断探索,直到迎来改革开放时代。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到1992年,也是跌宕起伏。这两本书连接起来,就是中国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之旅,阅读这两本书,就是让大家用历史逻辑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
看待西化与守旧之争,要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
历史强调具体情境。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说,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你们在阅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可能会认为,一些讲者的思想有些“幼稚”,例如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我们需要回到具体历史情境去看待这个问题,那时的一些人看到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的巨大差异,震撼之下难免会仰视西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亲身体验西方文明后,反而主张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大家有没有看到南大出版社的茶杯上有八个大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所以有这八个字,是因为南京大学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师在五四运动之后,与北大是中国思想界一南一北两大阵营。北大高举新文化大旗,要求革新,批判传统。南高师守护中华文化,被视为保守。南高师的老师,很多留学欧美,他们目睹了一个巨大的灾难——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西方文明就代表人类发展方向,那么为什么会酿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惨烈的战争?一战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也许超过二战,因为在当时,欧洲一代人没有了。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西方都是对的,对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是不能抛弃中国传统,而是需要扬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就是学衡派。
学衡派与新文化同人看似对立,但实际上是互补共进关系。问题在于,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中,传统的东西又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什么相结合?请注意不是简单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家阅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是否注意到鲁迅的演讲《无声的中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篇文字,特别是其中一句话,“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有没有人知道《无声的中国》这场演讲是鲁迅在哪里发表的?是香港。 1927年鲁迅在香港做了两场演讲,其中一场就是《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可能大家会有疑问,鲁迅此次演讲的内容例如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等,到了1927年已经不是新鲜事,他为什么还在讲呢?这是因为香港之行使他震惊了。内地早已深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香港还在“尊孔读经”。
1927年时,香港在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香港大学设立了中文学院。香港大学于1911年成立,完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香港大学“为中国而立”,实际含义是将英帝国思想文化传布于中国,但英国人也知道中国难以征服,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到20世纪20年代,广州成为国民革命中心,香港备受冲击。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1925年到1926年省港大罢工持续近16个月,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
省港大罢工期间,一位名叫罗旭龢的香港商绅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佳“解毒剂”,建议港英政府建立一个中文教育系统。把这个建议落实的是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和广东话,喜欢结交遗老遗少,动辄就讲中国传统文化好。在他推动下,香港大学成立中文学院,邀请前清翰林授课,讲四书五经。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英国统治者与华人精英勾结共谋,对抗五四宣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阻碍新思想新文化在香港传播,防止革命蔓延。因此,鲁迅在1927年看到香港原来是这样的,这才有《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守旧”和“西化”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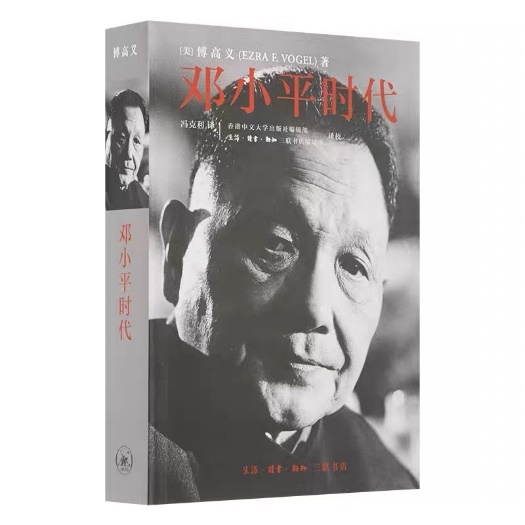
《邓小平时代》 [美] 傅高义 冯克利译 三联书店
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两个革命目标是富强与平等
第二本书是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代》。要讲清楚邓小平时代,必须要明白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聚焦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两个重要理想。第一个是富强,这个好理解。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欺凌,先是被英国打,到了1860年,中国首都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皇帝病死在承德,回京时已经成了一具棺材。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9.8亿两。半个世纪里,日本还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对于海外青少年来南京看什么,我们向有关部门提过建议,有个地方必须去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了就明白了,国家为什么要追求富强。
第二个目标可能大家不一定理解,就是平等。近代中国统治者用中华传统文化抗拒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少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却又拥抱马克思主义。儒家有个“大同”的理想,这和共产主义理想,有契合之处。《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儒家把未来设定在过去,从夏商周的“小康”,追溯远古的“大同”。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那个最血腥、最贪婪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也从共产主义理想的原始形态阐发人类未来走向。

从《邓小平时代》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线索,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这些问题,建议大家除了《邓小平时代》,还要读一读萧冬连教授的两本书《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和《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第二本书。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特区在1980年代初曾引起巨大争论。而市场经济的提出,更是一开始不敢直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换了个说法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曾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即计划经济部分先不要大动,在计划体制外另建一条通往市场之路。结果又产生了“价格双轨制”。一种商品有了两个价格,一个是由国家计划机关的定价,一个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后者高于前者。这就又产生了社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脑体倒挂”,吃财政饭的脑力劳动者不如小商小贩们赚得多,社会上有顺口溜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倒买倒卖,通过特权把计划内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88年国家决定搞“价格闯关”,准备“强行并轨”,价格都由市场决定。原本想法很好,还有配套措施,例如同时提升工资水平。但是忽视了社会心理预期。其实,前面没有白付出教训,“价格闯关”为后来价格体制的理顺做了先期准备。
到了1990年代,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政策受到质疑,他在1992年力挽狂澜,以87岁高龄,通过“南方谈话”拯救改革开放,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不动摇。“南方谈话”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犹如一层窗户纸被捅破。
1992年之后,中国飞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党领导的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邓小平“南方谈话”过去20年后,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来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遇到了结构性矛盾和历史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各自的困境,催生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球性议题。因此,中国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方向。从救亡图存走到今天,接下来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回望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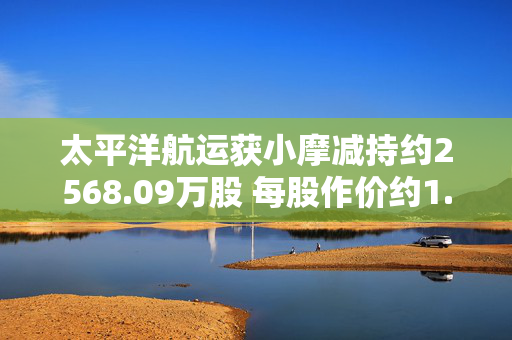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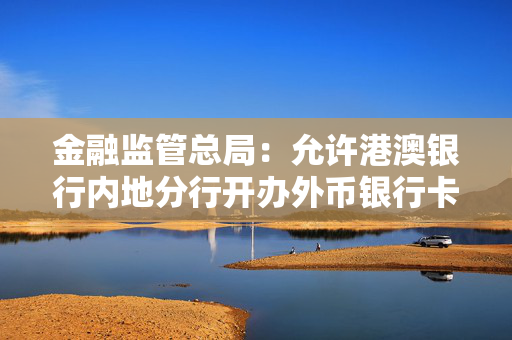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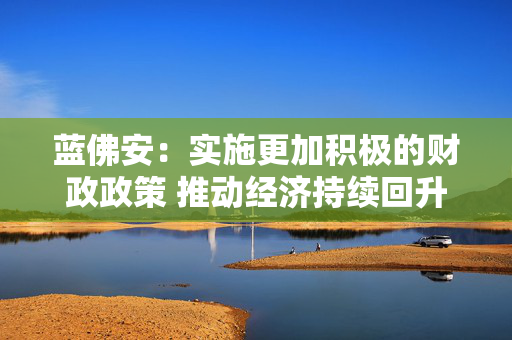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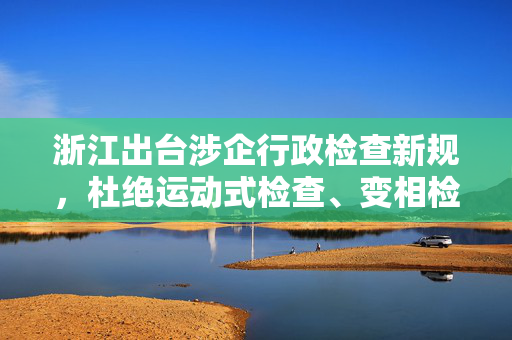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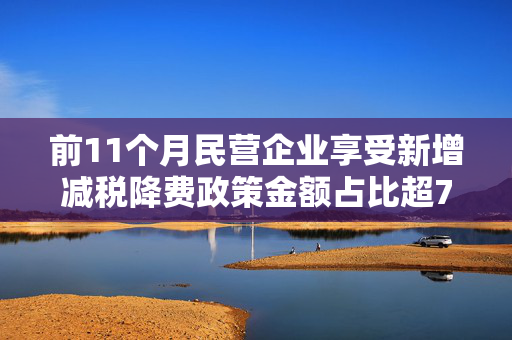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