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城市|早知虫有信
- 职场
- 2025-02-13 10:16:11
- 14
2024年底,去了次广东中山市,与老朋友叶克飞碰了个头。会友是表面,根本目的是实现我念叨了几年的夙愿,尝尝中山的禾虫滋味。
叶克飞是勤奋高产的专栏作家,作为广东人,也是个地道吃货。他近乎隐士般生活在中山这个“小”城市,最大爱好就是巡查他当做宝贝似的、散落在珠三角各地的百年乡村旧学校。好些年前,他就在群里炫耀中山的禾虫如何好吃,令我垂涎不已。这次抓到机会,当然不可放过。
最终,在中山一个相对僻远的乡镇饭店里吃到了禾虫,据称是一般外地人不太敢上口的生炒禾虫。禾虫的难得在于娇嫩,动辄“爆浆”,烹制难,运输也不容易,所以珠三角沿海地区之外很少见到。

生炒禾虫。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微信群里围观的朋友问味道如何。我实话实说:好吃是相当好吃,但不比东北的茧蛹更香。就口感来说,确乎独一味,很难找到相类食物。经常有人弄混禾虫和厦门等地的沙虫,这两种动物不仅在烹制方式和口感上大相径庭,在生物学分类上也差了好几条街,不吃不知道,一吃全明白。
广东吃虫厉害,我自幼便知。《神雕侠侣》中,杨过在华山之巅遇到洪七公,洪七公带他捉蜈蚣来吃,是书中经典场面。捉蜈蚣之前,交代了一句洪七公在广东的幸福生活:“那百粤之地毒蛇作羹,老猫炖盅,斑鱼似鼠,巨虾称龙,肥蚝炆老姜,龙虱蒸禾虫,翅生西沙,螺号东风,烤小猪而皮脆,煨果狸则肉红……”你看,禾虫赫然便在其中,而且与著名的龙虱为伍。
我在广州多年,却没吃到什么真正的特色虫子。曾到网上搜了搜,龙虱、水螳螂之类倒是不少,但一堆色彩斑斓的虫子,到家如何料理,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君子远庖厨,还是算了吧。
前阵子去西宁,逛夜市看到有专门的虫类烧烤或油炸摊。只能说“虫类”,因为显然不都是昆虫,甚至说“节肢动物”专项也不见得准确。比如禾虫就大幅超纲了。在摊前转了两三圈,犹豫要不要尝尝硕大的蜈蚣,是否如杨过在华山绝顶吃的蜈蚣那般“满嘴鲜美,又脆又香,清甜甘浓”。犹豫的原因真不是怕,毕竟我是资深的暗黑系食客,只是觉得这摊面与短视频常刷到的“东南亚特色吓人烧烤”过于雷同,又觉得此时充满了为猎奇而猎奇的刻意,完全没有杨过那般偶然撞见的惊喜。这么纠结着,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确过了啥都不说啥都不想张嘴就造的年龄。

油炸柞蚕茧蛹。
饮食之事,人都不免有个通病,就是看得到别人吃的怪异,却很难发觉自己吃得如何特别,非常本能和自然地双标。比如吃虫,我读到洪七公带杨过吃蜈蚣就觉得新奇得不得了,可没想过在东北吃茧蛹吃蝗虫,不见得比吃蜈蚣正常到哪里去。我第一次到长沙出差,在火宫殿里吃到炸知了。同行的四川籍和藏族同事皆肃然不肯动筷,觉得这食材简直不可理喻。后来我知道,四川有些地方嗜好吃一种“打屁虫”,真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有些上海朋友对作为食材的蛇和果子狸完全排斥,但对本地名小吃熏拉丝(蟾蜍)却可以从容领受,也是一个道理。

熏拉丝。
东北和南粤,一个极北一个极南,但我发觉有些食俗有很古怪的相似处。潮汕的黄豆酱和东北的大酱很相近,酸菜也有几分神似。至于吃虫,东北和广东是我见过对吃龙虱最为痴迷的两个地方。龙虱成虫在东北叫“老鳖”,又根据裙边纹理分为花盖(黄裙)和黑盖两种,后者说是不能吃,我猜是因为有明显的臭腺。龙虱的成虫和幼虫都是极为凶悍的水中杀手。成虫就我所知在南北很多地方都是被热捧的食物,样貌凶恶的幼虫长得肥硕油腻,却没听说哪里好这一口。我小时候问过长辈,说是因为有一股尿味。我虽然几次好奇心起,但终究没有冒着咬一口骚气的风险去尝试过。

黄缘龙虱。

龙虱幼虫。
食俗与文化是最容易绑定的,顺便绑定了高下坐标。依据某个族群的饮食评判其文明程度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比如,去西藏旅游的朋友对当地的风干牦牛肉,有些是委婉地表示“欣赏不来”,有些就说这是茹毛饮血,俯视之意溢于言表。
类似的俯视甚至歧视全世界遍地皆是,不奇怪。美国社会一度把越南裔移民的饮食习惯妖魔化得一塌糊涂,媒体上的话也说得非常难听,近乎直接怼“野蛮人”。市民丢了狗也怀疑是被越南移民偷去吃了,非常有“叫魂”的气质。
无论如何,食用虫类不大容易被承认是“高大上”的食俗。异地游客特别是来自大城市的游客,顶多有胆大的出于猎奇尝尝新鲜,但说到底,这不可能是“主流”、“文明”和“现代”的吃法。同样的,欧美人到中国吃猪下水做成的菜,多半也是类似的观感。
对于吃内脏、昆虫这些食俗,一种说法是来自历史上的食物匮乏。就是说,不缺食物的文明人是不会吃内脏、昆虫的,他们只会吃牛排和鸡翅这些最好、最“正常”的部位和食材。所谓“匮乏”所致,这说法就暗示了一种被迫的不自由。
吃内脏是否源于匮乏,其实很难讲。目前的考古研究结论,早期人类猎获大型野兽,比如野牛,如果离住地太远,无法全部运回,你猜,他们会优先带回什么?是内脏和脂肪。我们今天最宝贝的大块肌肉,首先被抛弃。其实看《动物世界》,狮虎猎杀动物后,首先吃的也是内脏。不是因为内脏柔软容易下嘴,而是对自然条件下生存的动物和人类来说,内脏的营养价值比大块肌肉要高很多。
不过,内脏的味道确实不见得好。这一点我曾有过一个偶然的观察结果。我自来爱吃各种内脏,也爱吃茧蛹、蚂蚱等昆虫。儿子小的时候,这些都给他尝过。几乎所有内脏,他都是尝过一次就不肯再吃。而茧蛹、蚂蚱等昆虫,他吃过后却还想吃,直到大了以后,才慢慢开始抗拒。这个个例或许可以表明,对一个基本没有口味偏好的小孩子来说,会因为内脏本身的特别味道自然排斥,如果后来能接受内脏,可能是社会文化的影响;油炸茧蛹等则相反,本来并无排斥,后来的排斥才是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

禾虫。
所以,“食虫”究竟是食物匮乏导致的被迫和不自然的“异食癖”,还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传统?我觉得,答案是“不一定”。比如,东北民间虽然喜欢吃龙虱成虫,却极少吃水虿即蜻蜓幼虫,而华北等很多地方都有食用水虿习俗。如果仅仅是匮乏导致饥不择食,那么没有理由水虿在邻近的东北不被当成食物。
对最早期的人类来说,虫类肯定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也许未来有一天还会是。吃昆虫是不是比吃牛排和鸡胸肉在文化上更“低级”?我只能说,在眼下这一刻,如此认知是可以理解的自信,从长期来说,却很可能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傲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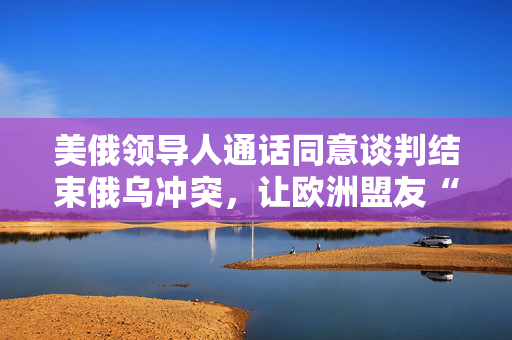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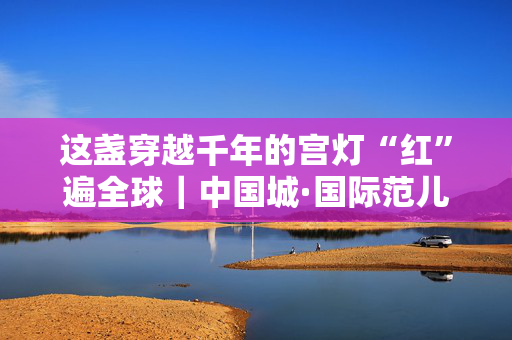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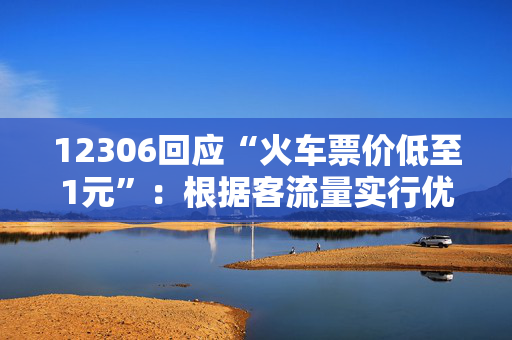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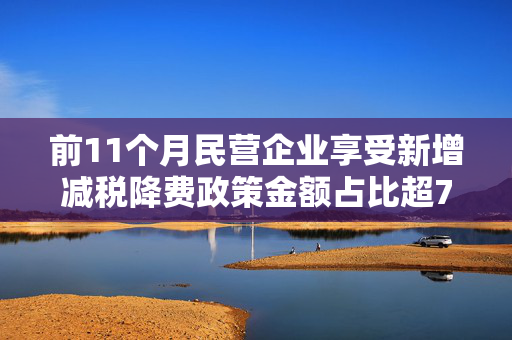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