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为形容词申辩
- 情感
- 2025-02-03 13:02:08
- 9
有谁可以说服大海
让它变得通情达理?
摧毁蓝色的琥珀、绿色的花岗岩
它能从中得到什么?
——聂鲁达《问题集·五十》
柯施(Kenneth Koch)有几行诗描述句子的诞生颇有趣味——
一天,名词们在街上扎堆儿。
一个形容词从它们面前走过,她黝黑美丽。
名词们看呆了,心动了,改变了。
第二天,一个动词开车过来,创造出了句子。
句子离不开名词与动词,但形容词往往夺走对名词的全部关注。使用形容词还是不使用形容词,这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涉及“生存还是毁灭”层面的大问题,就像蓝色的琥珀和绿色的花岗岩借诗人之口向大海发出的拷问。
于是,围绕形容词,拥戴者有之。
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不懂希腊文化》里谈到古希腊文学一代顶尖作家时,留下这样的赞美,“我们有萨福那些灿若群星的形容词”。
洛根·皮尔索尔·斯密斯《零碎二编》中有“形容词”和“修饰语”两则简短妙文。“唉,可偏偏为何我没能生在一个形容词的时代;为什么人们不再写银色闪亮的‘泪花’和月亮尾巴的‘孔雀’,不再写雄辩传神的‘死亡’和漆黑的用星星镶饰的‘夜晚’?”“玄妙的,夜晚游荡的,巨大的,蜂蜜白的——”“早晨的报纸摆在那儿没打开;我知道我该看看新闻,可我正忙得不亦乐乎,为的是找到一个描述月亮的形容词——那魔力般的,闻所未闻的,月亮的修饰语,也只有我才可能找得到或造出来,这样,小小寰球上的震荡与尘世纷争还算得了什么?”
钱锺书《人生边上的边上》评乔治·奥威尔《英国人民》一文,提到十六世纪法国人莫里斯·德·拉波特(Maurice de La Porte)出版了一部词典,“为学生作文之助;每一名词后注着一连串该名词应有的形容词”,词典名叫《形容词》(Les Épithètes)。钱先生引“英国人”词条下的形容词:“皮肤白的,骄傲的,与法国人为敌的,善射的,不肯服从的(mutins),有尾巴的(coüez),好战的(belliqueux),高亢的,脸色红的,躁怒的(furieux),勇敢的(hardis),胆大的(audacieux)。”钱先生评点道:“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发现这里面关于英国人身体的形容词都还适合——‘有尾巴的’除外,而英国人品性的形容词已经十九站不住了。”依钱先生之博览,他对此一节从未在讨论英国民族性的著作里得到征引表示遗憾。形容词甚至关乎“民族性”,关乎“民族心理学”。
当然,围绕形容词,挞伐者亦有之。
奠定依然通行于今的拉丁文“双名法”植物命名规则的林奈(Linnaeus),在其《植物学》中谈及植物的特征与命名时强调,植物的系统性分类是命名的基础;而描述植物的特征及命名则必然涉及“类比”与“形容词”。但是,“作为通称,形容词劣于名词,故不宜使用”。
董桥《英华沉浮录五·新闻记者十条指南》引亚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怎么当一名更出色的记者》第十条教记者删改润色原稿:“删掉‘非常’;尽量删掉形容词。记住法国人的至理名言:‘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
法国作家、《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更是一点情面不留:“不要奉承对诸如‘无法描述的’(indescriptible)、‘难以形容的’(inénarrable)、‘光彩熠熠的’(rutilant)、‘无与伦比的’(incomparble)、‘庞大的’(colossal)此类形容词的崇拜,这些形容词无耻地欺骗了被它们毁了容的名词:它们遭到淫荡的追逐。”
好一个“名词的敌人”。
好一个“名词的毁容者”。
好一个“名词淫荡的追逐者”。
语言中本来貌不惊人的“形容词”何来如此滔天原罪?
牛津大学富勒氏(H. W. Fowler)的《现代英语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欧内斯特·高尔斯爵士[Sir Ernest Gowers]修订二版,1965)不容置疑地为名词与形容词之间关系的主从性质定了调,为挞伐者提供了权威的语言法庭辩词,确立了名词的“傲慢”气焰。
“形容词,”《牛津大词典》说,“是这样一个词,它代表加给某一事物之名的某种属性特征,这个词会将此一事物摹状得更加完整、更加确凿,如一件黑的外衣。”果如此,形容词当为名词的好友。可实际上,人们说得没错,它们却成了名词的死敌。使用它们常常不是“将事物摹状得更加完整更加确凿”,相反,却令所摹状的事物更加模糊不清,带给它不必要的强化或限制;似乎使用形容词的人觉得,名词本身尚不足以令人印象深刻,或者素得没有色彩,或者也许更有甚者,仅仅满足于一个词而非可能用上两个词,这简直太可惜了……它们起到的唯一效果是削弱它们附加于其上的名词的权威……用形容词来扶持所有名词这一习惯,其最糟糕的情形可从这样一些词的搭配中见到,如不胜感激的谢意,真实的事实,通常的习惯,随之而来的结果,明确的决定,没有预料到的惊讶,在这里,形容词说着车轱辘轴般的话,没为名词增添任何意义……不停地与一个强调性的形容词交往,也就剥夺了一个名词以其自己的腿脚站立起来的能力。
因之,对于写作者,他给出了毫不含糊的告诫:“他应专注于他蛋糕的实质而不是拿小圆糖豆装点他的蛋糕。”
作为实词正宗的名词自然代表“实质”,而有着从属性质的形容词则只能充当“点缀”。难怪,英文中修饰“真理”和“真相”(truth)一词的形容词,用得最多的从来是几个规避藻饰嫌疑的词,如“干涩的”(dry,无藻饰的,无情感流露的)、“扁平的”(flat,直截了当的)、“光秃的”(blunt,率直的,直言不讳的)和“赤裸的”(naked,不加掩饰的)。
然而向上溯源,英语中大量重要的实词反倒是形容词做出的贡献,只不过在语言学家凯尔纳看来,那些“字词的形容词力量从视线中消失殆尽了”。
亚瑟·加菲尔德·肯尼迪(Arthur Garfield Kennedy)勾勒了英语形容词的名词化过程(即将形容词用作实词性的名词),虽然他无意探讨此一过程的原因与起始。
他先援引凯尔纳的《英语句法纲要》(Kellner, Outlines of English Syntax)谓:“凯氏列举了形容词被名词化的三种方式:首先,某物的特性过于显著,其形容词名称被采纳为实词本身。如‘黄金’最初指的是‘黄色的’(yellow);‘小麦’最初指的是‘白色的’(white);‘街道’最初指的是‘铺就的’(paved)。其次,语法结构的省略可以促成这一名词化过程。由于一形容词表达的是其所附属的那一名词的概念,该名词就被弃而不用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上帝’(the Almighty)、‘圣者’(a saint)、‘圣贤’(a sage)、‘好人’(the good)。最后,当形容词指称抽象概念时,即被用作名词,如‘善’(good)、‘恶’(evil)、‘不幸’(ill)。”
肯尼迪继而指出,名词化最可能的原因是出于“表达的简练”,把“the noble people”(高贵的人们)缩略为“the noble”,或古英语的“se besta guma”(the best man,最好的人)缩略为“se besta(the best)”,当表达十分流行且产生不了歧义的时候,这一做法尤为可能。《贝奥武夫》中大量的形容词用于指称被描述之人,即名词化形容词用作人称名词,为的是去掉不必要的名词。渐渐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之后,名词化形容词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特别是来源于法语并很长时间作为实词使用的词。乔叟时代,许多纯粹简单的名词即是从早期的形容词或分词发展而来的,而乔叟笔下大量形容词是作为单数抽象名词使用的。
无论“形容词名词化”是出于“表达的简练”抑或是“为了去掉不必要的”成分,这恰恰反映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谈及知识与文字的关系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三卷,关文运译):“人们在形成概括的观念时,多半在以简短而含蓄的标记,来形成得用的语言,以便迅速地表示自己的意思,并不在乎探求事物的实在的精确的本质。”由于实体或事物本身中“实在的本质”是不能为人窥见的,“都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因此各种名称所区分的各个物种的本质,“只是由人所形成的,很少与它们所从出的事物的内在本质互相适合”。这样,“事物的分类法完全是由人所造成的”。各种概括的名称只不过都是“名义的本质”。“文字的意义,和事物的实在本质,是不能精确地同一的。”
“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特殊的。”“一切名称(除了固有名称)既然都是概括性的,而且它们所表示的不是特殊的此一事物或彼一事物,而是一类一列的事物。”
“我们的观念愈概括,则它们愈不完备,愈不完整……这些复杂的观念是人们故意让它们不完全的……事物本身中所含的某些性质,在类别的观念中是故意被人舍掉的。因为人心既然想形成概括的观念,来包括各种特殊情节,则它便不能不把时间情节,空间情节,以及使它们各不相通的那些情节除掉,同样,它如果要形成更概括的观念,以便包含各个物种,则它又不得不舍掉那些使各个物种互相差异的那些性质,又不得不在那个新组合体中加进各个物种所共同的那些观念。”
洛克区分了“简单的观念”与“复杂的观念”,认为前者“最不含混”,后者“容易含糊,不确定”。
“简单观念的名称所表示的那些观念各个都是一个单独的知觉,因为它们并不参照于任何实体,只参照于它们直接所表示的那个知觉。所以,它们最不含混。”“简单情状的名称亦是这样。”
人心在形成复杂的实体观念时,其所集合的各观念的数目,会因造作观念者的注意力、勤奋、想象而有所差别:“人们普遍都安于少数可感的性质;至于别的性质纵然亦很重要,纵然亦同人们所取的那些性质有同样紧密的联系,可是人们往往(纵不是经常地)把它们忽略掉。”
“最不含混”的简单的观念“都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名称;而按文法学者的说法,抽象的就是所谓名词(substantive),具体的就是所谓形容词(adjective)”。
名词和形容词平等的简单叠加,抽象和具体平等的简单叠加会营造出怎样复杂的“心灵景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诗人马致远脍炙人口的散曲小令《天净沙·秋思》被同时代评家誉为“秋思之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显而易见,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九个名词构成景语;枯、老、昏、小、流、人、古、西、瘦,九个形容词将前者点化成情语。
何以景语能必然转换为情语?王国维对此隐而未发,但诗人克莱恩(Hart Crane)却将其道破:“即使那个时期,我的诗歌——就其真正地富于诗意而言——也会避免使用抽象标签、用事实术语表述经验等——它必然会用更直接的身体-心灵经验的术语来表达其概念。如果不是这样,它一定会失去其影响力并变得太过直截了当了。”(哈特·克莱恩1926年3月17日致戈勒姆·蒙森信)
景语者,“使用抽象标签、用事实术语表述经验”;情语者,“用更直接的身体—心灵经验的术语来表达其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景语”大致呼应着弗兰茨·布伦塔诺所谓的“物理现象”,“情语”则大致呼应着他所谓的“心理现象”。
依照布伦塔诺,“物理现象”指的是广延性和确定的空间位置。它们只有通过外知觉而被知觉。它们仅能呈现为不同的诸多现象而不能呈现为同一现象的不同构成成分。“心理现象”指的是由内知觉而把握的现象。它们是唯一一种能被真正“知觉”到的现象。它们只可能为单一个体所知觉,也就是说,不同个体有着不同的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总是以一种统一整体的面目呈现于人的内知觉。作为“物理现象”的一般性“景语”最终得以汇入作为“心理现象”的特殊性“情语”的“统一整体”之中。
维特根斯坦不认为存在纯粹的颜色概念本身。“我对待颜色概念就像对待感觉概念。”(《论颜色》[Remarks on Colour],第三部分,71则)只有这样,往往归于物理性的颜色才可能与唯有心理性的感觉水乳交融地化为独特体验的织物,在此一体验织物的整一中,主观与客观消弭了人设的界限。
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第四章,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辞别忏悔神父,思绪万千,离开多利蒙特的大路朝大海走去。走过薄木板搭成的桥面,海风瑟瑟,为避开令他恼怒的思绪的纠缠,他转过脸,侧身望着桥下打着漩涡的清浅水流。
他从自己的珍藏里抽出一个短句,轻声自言自语:那从海上飘来光影斑驳的云彩的一天。这一短句与这一天与此情此景在一个和弦里和谐交融了。词语。这就是它们的颜色吗?他让它们亮起来又暗下去,一种颜色接着一种颜色:朝霞的金黄色、苹果园的赤褐色和绿色、海浪的蔚蓝色、羊毛般云朵镶了流苏的银灰色。不,这不是它们的颜色:这是这个时代本身的沉稳和均衡。难道他喜欢词语抑扬顿挫更甚于词语传说与颜色的联合?抑或是,由于他视力弱,一如他不强的心智,他从那绚烂的感觉世界透过五颜六色的、蕴积丰厚的语言棱镜呈现出的折射之中所得到的乐趣,比不上他在一篇明白的、流畅的、句子完整的散文之中静观那完美映照出的内在情感世界所得到的乐趣?
“颜色”和“形容词”本质上是相通的,其相通处正在于两者均拨动了个体心理中最为敏锐的“感觉”的心弦,达成了卡尔维诺所谓的完全基于形容词的“心理的精确缜密”。可以说,基于此理,清诗人杜濬《变雅堂诗集》卷七《山晓亭记》摹写出了时间之中名山所呈现的万千气象:“钟山者,气象之极也。当其明霁,方在于朝,时作殷红,时作郁苍,时作堆蓝;少焉停午,时作乾翠,时作缥白;俄而夕阳,时作烂紫,时作沉碧;素月照之,时作远黛,时作轻黄。”(钱锺书《中文笔记》第一册)同样基于此理,芥川龙之介摹写出了空间之中他感情的生命之川。“银灰色的雾霭,青油似的河水,喘息般的飘渺的汽笛,运煤船焦褐色的三角帆——这一切唤起难以抑压的哀愁的水上景观,是如何使自己幼小的心灵激动得犹如岸边杨柳震颤的树叶啊!”“有了大川的水,我才得以生活在纯粹而本真的感情之中。”(《妄想者手记·大川的水》,陈德文译)
无独有偶。业师李赋宁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发表《乔叟诗中的形容词》一文。文章切入点看似微末,但其独运的文思,如高手剥茧抽丝,一丝不苟、层层深入,清晰、干净的文笔下幽幽溢出厚重学识的至味,令人回味无穷。
此文从美国文学批评家楼衣勒(J. R. Lowell)在乔叟诗里发现的“一种纯粹是春季的气息”起笔,紧紧抓住乔叟诗歌中“形容词”之诸面相(颜色形容词、光明与黑暗形容词、感觉形容词、难以归类的其他生动的形容词,以及形容词与它所形容的名词相互之间位置的安排),依据对诗歌文本细致入微的分析,探究了这一“纯粹是春季的气息”之所以形成的艺术奥秘。
李先生认为,乔叟是一个“善用颜色的画家”。形容词正是他“绘画”使用的颜色。“乔叟的某些形容词不仅本身生动传神,而且容易激发读者的思想和感情,使被描写的事物获得更加丰富复杂的内容。”洋洋洒洒举证剖析之后,李先生言简意赅作结说,颜色形容词在乔叟诗行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因此使他的描写更加色彩鲜明而美丽了”,“由于采用了中世纪的一种修辞手段‘否定法’(correctio),他就有可能把一系列的形容词聚集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加深、加多他所描绘的图画中的颜色效果”。“他对于语位转换和部分语位转换做了巧妙的、多变化的运用”,“收到了很大的艺术效果:鲜明生动,强调,声音的和谐、均衡、对照,等等”。而正是通过对表示光明的形容词(如bright和clear)、表示感觉的形容词(如sweet,fresh和new)以及颜色形容词“巧妙的选择和艺术的安排,乔叟才有可能把楼衣勒所赞美的那种‘春天的’芳香灌注到他的诗行里去”。(《漫谈西方文学》,北京出版集团,2018年5月)
“形容词”渐渐凝结为文本的气息,文本的气息再一次别出心裁地凝结为作家的“风格”。
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表达的俭省”推崇备至。他精准揭示了“简约大师”风格的“不可思议”,点出了“形容词”的变化在其风格形成中扮演的不可忽视的角色。
他有办法将观念和充满诗意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原本无以复加的繁复浓缩为常常不过数页篇幅的文本:或叙述或暗指的一个个事件,无限之境令人目眩的杂多闪现,还有种种观念、种种观念、种种观念。此等的稠密何以在其澄湛得清晰、遣离了藻饰、一无窒碍的语句中传达得毫无淤积之感;其简短、跑题的叙述风格何以导致其语言的精准与具体,而这一语言的别出心裁则通过节奏之变化纷呈、句法行进之变化纷呈、往往意想不到和令人惊异的形容词之变化纷呈得以映照出来;所有这一切汇作一种风格上的不可思议,这一不可思议在西班牙语中无有匹敌者,而独独博尔赫斯悉知其秘方。
“知识性散文诗”的开创者、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出版于1991年的随笔集《双城记——谈流亡、历史及想象力》中有篇过目难忘的文字,题目叫作“为形容词辩护”,篇幅不大,内容深刻精彩,容我从1995年莉莉安·瓦莉(Lillian Vallee)的英译转译如下:
人们常对我们说要划掉形容词。自身过硬的文体,据说,用不着形容词撑门面;名词的坚韧之弓配上动词的疾驰且无处不在之箭就够了。然而,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如同一间外科诊所,到了星期天不免悲凉忧伤。蓝色的光从冷森森的窗口渗出,一只只荧光灯发出窃窃私语。
对于极权国家的士兵和发号施令者,名词和动词足够了。因为形容词是人与物之个性不可或缺的保证者。水果摊上我看到一堆瓜。在反对形容词的人那里,这件事本没什么难处。“瓜堆在水果摊上。”可就在这同一时间段里,一只瓜,像维也纳议会致辞时塔列朗的肤色,黄不拉叽的;另一只瓜,绿油油的,尚未熟透,洋溢着青春的傲慢;还有一只瓜,双颊塌陷,迷失在深深的、忧伤的静默里,仿佛它受不了同普罗旺斯的农田分手。瓜与瓜没有两只会是一模一样的。有些是椭圆的,有些是矮胖的。有些是硬的,有些是软的。有些散发着乡村的、晚霞的气息;有些则干瘪瘪的,一副无可奈何,为一路贩运、雨打、陌生之手、巴黎郊野灰蒙蒙的天空搞得精疲力竭。
形容词之于语言,正如颜色之于绘画。地铁车厢里坐在我身旁的那个上了岁数的人:就是完整的一串形容词。他假装打盹,可透过似睁非睁的眼睑,他在观察同车的乘客。他双唇绽露出一丝顽皮的微笑,时而这微笑会变得怪怪的。我琢磨不透,他内心沉积的是镇静的绝望,是倦怠,还是不急不慢的幽默感,就连时间的流逝也拿它毫无办法。
军队限制形容词的数量。在它没有颜色的眼中,只有“一样的”这个形容词才受到青睐。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来复枪。一个军训归来的人,换上平民的衣装,只要在彬彬有礼的城市里迈开第一步,他就会记起那不可思议的爆炸,这爆炸出自形容词、颜色、光影、形状和种种的千差万别,而充满独特个性的宇宙正是用了这些来问候他。
形容词万岁!微不足道的或举足轻重的,为人遗忘的或仍在流行的。我们需要你,可塑造的、纤巧的形容词,轻轻附着在物与人的身上,永远呵护着不让个性生机勃勃的味道走失掉。酷烈、苍白的太阳下淹没了的背阴的城市与街道。鸽翼色的云朵和大块大块蓄满了狂怒的乌黑色的云:要不是千变万化的形容词在你们身后飘荡,你们还能算得上什么?
没了形容词,伦理学领域一天也存活不下去。善的,恶的,狡诈的,慷慨的,报复心切的,激情洋溢的,高贵的——这些词就像是断头台的利刃寒光闪闪。
多亏了形容词,不然记忆亦将荡然无存。记忆是由形容词构成的。一条长长的街,一个灼热的八月天,一扇嘎吱作响的门通向花园,花园里,蒙着夏日土尘的醋栗间,是你们的机敏的手指(对了,“你们的”也是一个所有格形式的代词)。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可能过一辈子也不见得他的色盲会被注意到,直到一个特殊的机会将其暴露出来。”(《论颜色》,第三部分,31则)对心灵而言,形容词给予我们的正是这一特殊的机会,它们让思想与想象的敏锐性摆脱不知不觉的平庸,摆脱“色盲”毫无征兆的梦魇。
借了“形容词至上”一文,齐奥朗(Emil Cioran)更是在人的智力进步与人的文明进程中为形容词找到了安然栖息的居所——
我们一直在受苦,但按照重要哲学时刻所持有的普遍观点,我们的痛苦要么是“崇高的”,要么是“合理的”,要么是“荒谬的”。痛苦构成了一切有呼吸者的肌理;但其形态已改弦易辙;它们构成了一系列不可简化的表象,使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他是第一个遭受这种痛苦的人。对这种独特性的自豪感促使我们珍视我们自己的痛苦并且忍受它。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对于他人而言,每一个人都是唯我论者。苦难的独特性取决于在词语和感觉的总和中将其孤立起来的语言的特质。
限定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智力的进步。将它们全部压制掉,文明还剩下什么?聪明和愚蠢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形容词的运用,使用形容词而没有多样性,就会造成平庸。神自己只靠我们加给他的形容词而活着;这就是神学存在的理由。因此,通过变着花样调节自己痛苦的单调,人只有充满激情地寻找几个形容词来向心灵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这种寻找是可怜的。表达的贫乏,即心灵的贫乏,它体现在词语的匮乏、词语的枯竭和词语的退化中:我们用来确定事物和感觉的那些属性,最终太像一堆堆语言的腐肉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未尝试过的感官和我们天真的心灵认清自己并在限定词的宇宙中感到高兴,它们就会在形容词的助力之下同时也冒着形容词带来的风险蓬勃发展,要知道形容词一经被剖析,即证明自己是不充足的,是匮乏的。我们说空间、时间和痛苦是无限的;但无限的这个词的意义并不比美丽的、崇高的、和谐的、丑陋的……更重要。试想我们强迫自己去看清文字的底部?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每一个词语都脱离了广阔而肥沃的灵魂,它变得毫无效力。通过向文字投射一定的凝聚力、打磨它们并使它们闪闪发光,智性的力量发挥出它的作用。)
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物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在《心灵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Mind,高觉敷译)中谈到心理学家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黑猩猩与儿童)所发现的行为之中可称为“本能”的两个活动:一是“好洁本能”,即避免污秽的行为;一是“装饰本能”,即苛勒阐释过的——“原始的装饰不欲借以刺激他人的视觉,而欲赖以增高自己的身体的情感、威严及自我的意识”。
竭力维护名词之尊严或许是人类“好洁本能”的自然延伸;那么,为形容词申辩或许捍卫的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装饰本能”的必然。
罗兰·巴特深深理解这种“必然”。“不要漂白语言,而要品味它。轻轻地抚摸它,甚至梳理它,但不要‘净化’它。我们可能更喜欢诱惑而不是哀痛,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认识到有需要诱惑的时候,有需要形容词的时候。或许‘取其中’就是:接受谓词,把它视为不过是一个片刻而已:一个时间段而已。”
的确,倦怠的人类有需要形容词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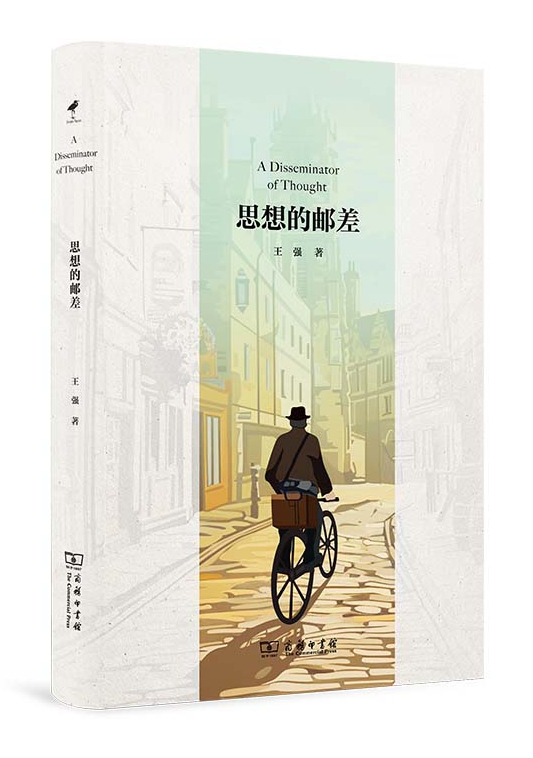
本文摘自《思想的邮差》,王强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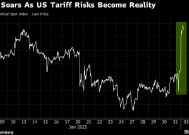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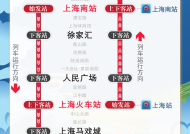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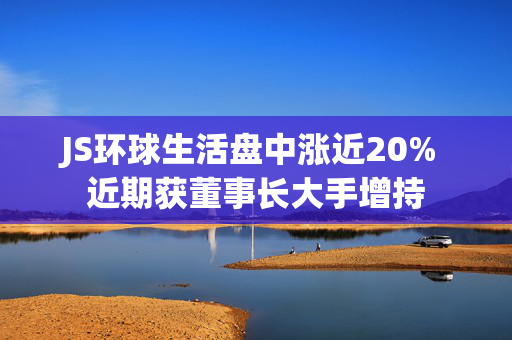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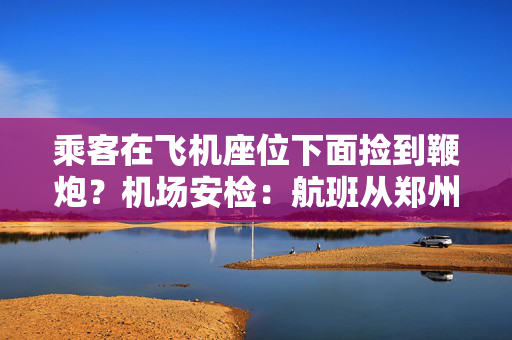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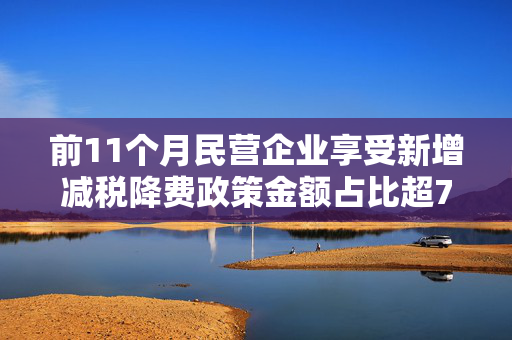







有话要说...